我的家乡,坐落在莺脰湖的西畔。莺脰湖,又名莺湖,其名之雅,源于一则流淌了千年的传说。相传春秋时,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,携西施泛舟五湖,曾在此停泊。西施于船头抚琴,琴韵悠扬,引得莺鸟盘旋不去。一只黄莺沉醉于天籁,俯首啜饮湖水,不慎浸湿了脖颈——古称“脰”,其优雅倒影与潋滟湖光相映成趣。范蠡见之,遂以“莺脰”名之,将这片刻的诗意永远镌刻在江南的烟波之间。

湖中曾有二岛,犹如碧玉盘上的双珠,各具灵性。其一曰平波台,建制可考至明朝天启二年,始筑于湖心。至清代,又重建佛殿楼阁,垂柳依依,遂成一方名胜,是文人墨客观湖赏月、品茗抚琴的雅集之所。相传古时水患频仍,有高僧于此筑台诵经,镇风波、护舟楫,故得“平波”之名。那方青石棋盘上,仿佛还残留着未尽的棋局与吟诵的余韵。
关于此台的神异,民间亦流传着另一种说法。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,平波台乃一只神龟所化,始终漂浮于水面,无论湖水如何涨落,从不沉没。记得有一年大水漫溢,岸边公路尽数淹没,平波台却依旧静静浮于湖心,如龟负天书。这传说在我心中,因母亲的亲身经历而愈发真切。她曾说起,十四五岁时随大人摇船去湖南岸劳作,在船尾不慎失足落水。母亲不谙水性,只能在湖中挣扎。她说,那时仿佛脚下有物稳稳托举,使她始终不下沉,如同踩在一只巨龟的背上。约莫半个时辰后,才被后来的船只救起。这段往事,为平波台的传说添上了一笔温暖的、属于我们家族的亲证。
另一岛名黄漾墩,正是传说中神莺驻足之地。岛上蒲草丰茂,水鸟翔集,每逢春深,便有新莺啼啭,似在殷勤追寻先祖的仙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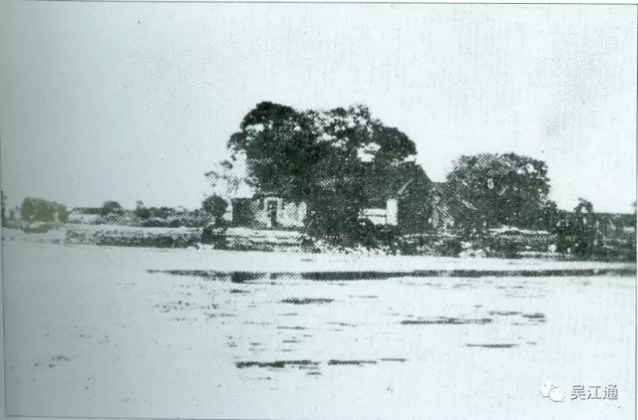
此湖风光,曾令无数才子帝王心折。唐代李白、明代汤显祖、清代潘耒等文人雅士都曾在此驻足,留下瑰丽诗篇;即便是南巡的乾隆皇帝,亦为之动容,挥毫咏叹“莺湖夜月”之空灵。这“夜月”之景,为古“莺湖八景”之魁首,其余如“殊胜晓钟”、“远浦归帆”等,无不诗情画意。及至明清,湖畔人文臻于极盛。每逢端午,湖上龙舟竞渡,画舫如织,鼓声震天,欢声笑语与粼粼波光交织,那是水乡独有、令人神往的活力与丰饶。
这些传说与盛景,并非只存于故纸堆中,它们曾真切地活在老一辈渔民的呼吸里。小时候,每到银鱼汛期,便是丰收的盛典。渔工们古铜色的脊梁在晨曦中闪烁,他们呼喊着铿锵的号子,协同发力,将沉甸甸的丝网从湖中拉起。当渔网脱离水面的刹那,景象堪称奇迹——仿佛将整条璀璨的银河从湖底捞起!无数银鱼在网中剧烈跳跃,通体晶莹剔透,在朝阳下迸发出令人窒息的、纯粹的银光。整个码头随之沸腾,银鱼入舱的噼啪声、水花的溅落声、人们的欢呼声,混合着湖水与鱼获的清新腥气,共同酿造出湖畔独有、足以烙印一生的丰收狂想。
然而,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传统的堤岸,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这片水域的容颜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,推土机的轰鸣取代了悠扬的渔歌,西北岸的大片湖水被填平,建起了规整的莺湖公园。九十年代,北岸的小九华寺在旧址上重建,飞檐斗拱,金碧辉煌,成为一方香火鼎盛的道场。
最令人痛心的是,那承载着镇水传说、数百年文脉与家族记忆的平波台,也被彻底铲平,原址上崛起了现代化的酒店与住宅区。那座曾见证无数诗会与雅集的古亭,那些未下完的棋局,连同神龟护佑的传说,都永远沉入了水泥地基之下。神莺驻足的黄漾墩也难逃厄运,被推平后开发为商业地产,只在原址附近象征性地建了一座双莺亭。夜风过处,亭铃呜咽,不似吟唱,反倒像是对故园永无休止的哭诉。
小九华寺东面又一轮大规模的填湖开发,使湖面急剧萎缩。新建的“湿地公园”旁,几个大型楼盘的倒影取代了摇曳的芦苇。湖水在持续的喧嚣与侵扰中渐渐富营养化,那曾经如银河倾泻般的银鱼群,终于消失在不断被割让与污染的水域里。
几十年来,我依旧守着它秋日里勉强残存的那份静谧。林立的桅杆早已消失,龙舟竞渡的鼓声也早已沉寂,如今唯有公园里传来的广场舞乐曲与寺院的钟声,交织着记忆中的渔歌,在复杂的湖风中飘散、融合。
黄昏时分,我漫步于那段侥幸留存的天然湖岸。夕阳如血,悲壮地浸染着湖面。我仿佛透过时光的薄雾,再次看见平波台上的棋局未终,黄漾墩上的新莺初啼,七桅船正张满巨帆,缓缓驶入霞光深处。莺脰湖的波光里,沉淀着千年的琴音、帝王的诗赞、龙舟的鼓点、镇水的祈愿、一网银色的辉煌,以及我们所有人共同经历却又无力挽回的、巨大的时代倒影。
今日提笔,并非只为发思古之幽情,更是志在让更多人知晓并记住:这曾美如诗画、灵动鲜活的莺湖八景,这片水域所承载的,是我们不该遗忘的江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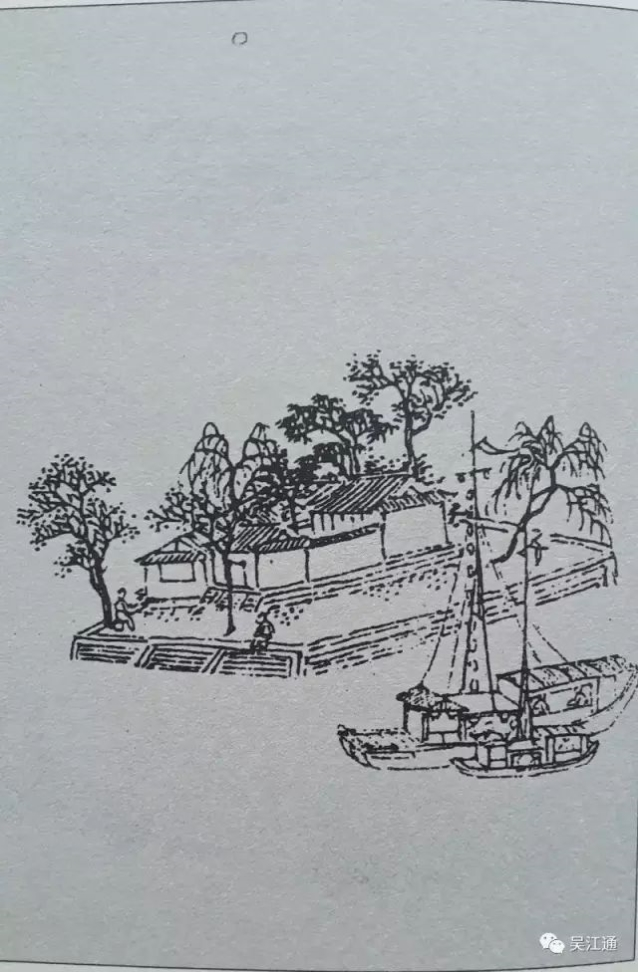
![]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