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白鱼潭漫记》
昨天周日,秋阳暖得正好,跨上小电驴往白鱼潭公园去。刚到门口,一阵歌声便传了过来——几位老太太捧着歌谱,正合唱《军港之夜》。苍老的调子虽算不上字正腔圆,可那份摇头晃脑的投入,倒像捧着宝贝似的,热热闹闹里透着股自寻乐趣的劲儿。没见带音响,就凭着嗓子亮开唱,许是一群舍不得买设备的老人,却把寻常日子过出了滋味。





绕着公园转了圈,中心的荷花塘边最是热闹。大小平台上,广场舞的音乐此起彼伏,红的绿的裙摆随着节奏起落,衬着塘里残荷,倒成了秋日里最鲜活的画面。
转到另一边,几位“老柴头”“老太太”的装备就齐整了:60寸的大屏幕立着,旁边还支着15寸的小屏,功放机嗡嗡作响。一位老太太正对着话筒唱,声音洪亮得有些刺耳,惊飞了塘边两只白鹭。听了片刻,忽然懂了周边居民为啥在“南太湖论坛”上吐槽——这般不遮不拦的唱腔,确实少了些婉转。好在没多久,一个“老柴头”接过话筒,一开口便见功底,声调顿挫悠扬带着韵味,总算驱散了先前的嘈杂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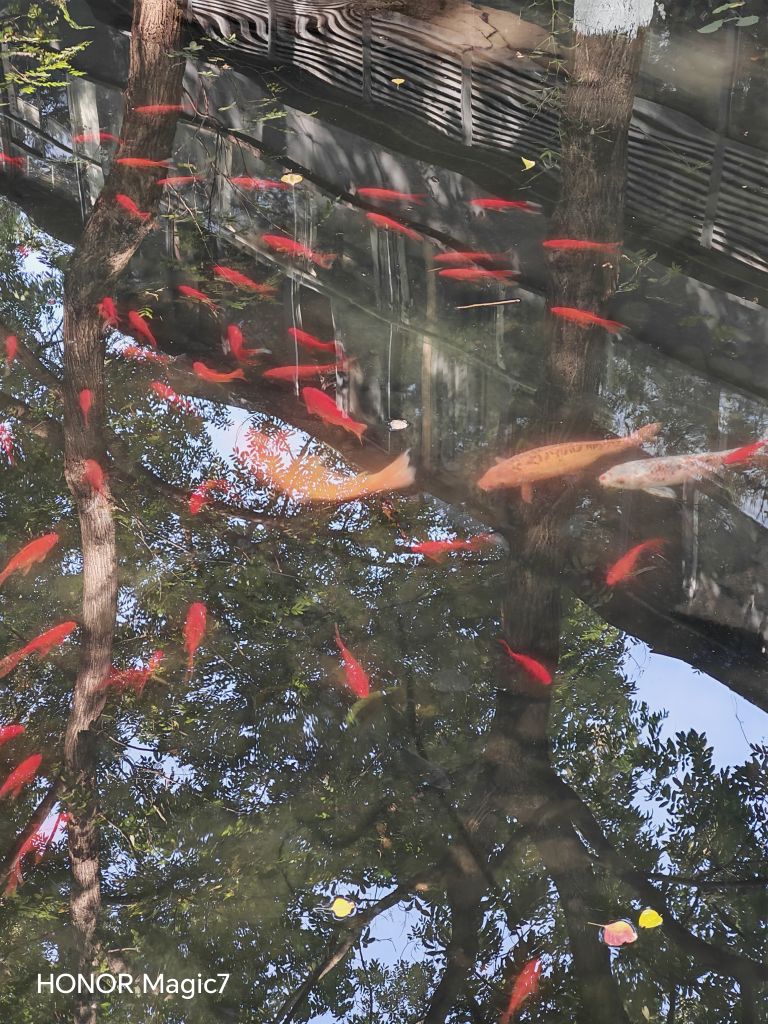
正走着,忽见一支歪脖子树枝上吊着个人。那人一只手弯曲着紧扣树枝,身子像刺猬似的蜷成一团,头埋在胸前,离地足有两米多。我赶紧掏出手机拍了张照,还没站稳,他已像猴子般“噌”地跳落地面,转过身来与我打了个照面。我忙竖起大拇指,他笑得满脸舒展,精神头足得很,下巴上留着六七寸长的胡须,黑白相间,倒有几分仙风道骨。“您这身手可真厉害!”我忍不住赞叹。他摆摆手,嗓门洪亮:“年轻时在少林寺练过三年,砖石都能轻松击碎。”他说自己从山东来,今年64岁,平时在附近帮人装修,挑沙泥、扛水泥、搬砖头,昨天刚好歇工,来公园透透气。


![]()